御药房比平常更忙碌。
因为除了由莲的药品外,为了对面的东篱殿的药品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上官应雨病了,得了風寒,正在高燒不起。
他在臥床上躺了一夜,有奴才為他蓋過被子,但幾次看見了地上的絨被,是他掀開丟去的。這嚇壞了那些可憐的奴才,他們馬上為他叫來太醫診病,但他每次都拒絕了。他冷冷的回應讓奴才們不知所措。
裴謹來到東籬殿時看見了他病得嚴重的樣子了。奴才們個個跪地叩頭,久久不敢起。
可最後裴謹還是沒有發怒,只是下了令,命藥師配出立即見效的苦藥。
現在裴谨下了朝,直接移驾东篱殿。
而裴谨见到他时,宫婢速速跑来禀报,说他精神不振,醒來後又睡過去了。
裴谨聽完很自然地拦下奴才叫醒他的行動。
他一人踏入东篱殿内门,入到厢房,走近去躺着睡人的卧床。
他也怕惊动到空气似的,连坐到床边的动作都是极慢极轻的。他抬手,轻轻拈了拈绒被。
床上的人眉头蹙起,嘴角一直抿住,看着像是难受至极而晕过去的。
很久没如此安谧了,这个东篱殿。就算每天的同床共枕,却不无同床异梦的夜。他一醒来,这个东篱殿充斥的,仍是冷得发寒的空气。
裴谨扯起涩笑,刚要抚下睡颜的手还是收了回来。
他還不會相信這個上官應雨,因為他太聰明,讓他防不勝防。
第一次不相信他,第二次也不会,第三次还是不会。不过再也不会有第四次,因为狡兔终于是学乖了。
他点了上官应雨的睡穴,让他睡得更沉,再将他扶起。旁边的奴才将热好的药递给他,他小心撬开那个好看的下颌,举勺放至他嘴边,看着一勺勺的黑色药汁终于入了口下了喉。上官应雨是睡了,但舌头出于本能,偶尔会把藥汁顶回去,裴谨见状,就俯身,低头将那些药汁,一次次哺下去。
药真的苦,连裴谨自己也无法忍受,一张峻脸少有地有了不舒服的表情。
夜又来了。
裴谨在上官应雨醒来前就离去了。現在他犹豫着要不要去静容轩一趟,边走边想,恰好走到了琉离阁。
他抬眼望去那紧闭的阁门,没有侍卫的看护,也没有婢女的迎候,只有越发茂密的树枝横生而出,遮住了这扇大门的顶端。
若不是他知道这里住着主子,他以为这里已经许久不曾有过生气了。
一阵苍凉。
侧头向里探眼,屋里有轻轻跳跃的火光,伴随着里面动作不大的人影,裴谨只感到一阵生涩。
一阵笛声。
清幽淡雅的乐音。它响起。
当伫定脚,细听,裴谨倏地想起了一些……往事。
这悠悠清笛,不就是他深埋在脑里,久久不曾打算再浮起的记忆划痕么。
裴谨怔住,再次拦下了太监的宣侯,站在枝下,隔着厚重的大门,窃听那毫无作备的笛乐。
裴谨至今的记忆里还是会有一些不让他忘记的事情。
比如说,他的品妃。当初两人像青涩竹马那样手拉手走闹市里逛,采花灯,猜哑谜,画纸鸢,仅是这些,他记得当时乐得合不上心。
又比如说,时过两年后,他登基称皇。一次随亲王微服出巡那次的遭遇。
一天独自跑去了外林狩猎,一箭射去丛林深处,中了!他高兴过去探看成果,是一只已断气的犬崽。很小的一只,箭直穿过它的身体,裴谨拎起它时,它的四肢还能挣扎了一下。
“你……”
身后有声音。裴谨回头,只见一身穿不俗的少年楞楞站在面前,眼里怔怔看着裴谨手里的犬崽。呆滞眼神立即锐如刀尖,恶狠狠怒视裴谨:“你竟然,杀了它!”
裴谨看了看犬崽,还来不及转眼看向少年,身体就被猛地推倒!背后是坚硬的岩石,裴谨痛得几乎翻出白眼。
抓狂的少年对着他就是一通乱打,击击中骨。他一咬牙,一翻身,将少年死死摁在地上。
少年无法动弹。
“……你是谁?”裴谨压近少年耳测尽量冷静审问。
“是我问你是谁!这里是我家的后林,你擅闯民宅,还扼杀了我的小狗!”少年气得通红的脸被裴谨毫不怜惜地压在了林土上,幸好上面落了一地的红叶,少年的脸才免于被擦伤。
裴谨四处望望,果然望到了园林出口处立著名为佟宅的门匾。
他意识到自己是误闯了他人地方了。但仍能感觉到少年的用力挣扎,裴谨还不太想放开他。
“是我错,我道歉。”摔落在旁的犬崽的尸体已经一动不动,哼声都没有了。它半睁着眼,眼里闪出死前的悲伤。
少年一同悲伤。
“它才出生不久……它的母亲也已经病故了……”他呜呜发出轻咽,眼泪渗入到清新的土里。
裴谨第一次有了发自内心的愧疚。怪自己一时不听劝,非要去自己所想之地,为自己所想之事。“对不起,我把他安葬了,再送你回去。”
裴谨把马拴在一棵树旁,找来了一杆枯死的树干。少年抱着犬崽低头坐在一旁。裴谨摸出配在腰间的短剑,脱鞘,扬手一挥,树干被劈出一个斜角。他看了看,觉得可以了,收起短剑,握起树干,一发力狠栽进土里。
由于常常有习武练体,裴谨的力气也变得强蛮。
不久,一个不深不浅的坑穴挖好了。
裴谨直起身,一丢树干,边擦着额头粗汗边走向少年:“给我。”指少年怀中的犬崽尸身。少年抬起红肿的眼望他,他刚好背着阳光,站在自己面前的身形高大英伟。一双手刚刚劳动完,已满是尘土,但手背的管脉更清晰可见。
少年瞪他一眼,自个儿起身,将亲自动手下葬。顿了顿,往衣里摸摸,摸出一块锦巾。上面的花纹零零乱乱的,但还是能看出是几株白玉兰。用它将犬崽尸身包裹住,再小心放入坑里。
裴谨看着他,看似完了,就又拾起树干,一堆一堆泥土再填回坑里。
少年都不与裴谨说话,裴谨也不会再找无趣,就牵着马陪着他一路走出园林。
方才在园里被树叶挡住光线,出来一看,夜幕原来已经降临。
裴谨干了活出了力,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。少年撇他一眼。他在裴谨干活时观察过,看衣装,不与自己相差,甚至,那身衣服还可能非达官也要是贵人才穿得起的贵气。然后看他身上的装饰,玉坠佩环不说,仅是他刚刚亮出的短剑就足以衬出他身份的高贵:他一定不是武侠,但武功必定不轻;他随意用那剑砍伐俗物,看得出他幷不珍惜那剑。不是武侠却又能玩武随性,这个人,一定大有来头。
这是少年平常跟随父亲见面于官场之士而得来的见识。
但就算如此,少年也不打算懦怯。
裴谨立即不高兴了。这种失态虽然不可避免但还是有损他身为龙子的威严的。
“你还没回答我是谁。”少年突然又问起来。
擅闯他人地方是此人有错,猎杀动物更是此人犯下的罪。在少年看来,任何生命同等价值。而那只小狗,是他现在唯一的朋友。
他有苦衷。
裴谨眼中深幽,似在定睛少年身上,又似乎在游移。
“公子来猜猜在下是什么人?”
少年却转头,不再与他搭话。裴谨好玩似得嘻笑一声。
大宅门口,一名女子焦急地踱来踱去等在门外。
“玉兰,我回来了。”少年一到立即化开笑脸,朝那女子一唤。那女子一转头看,见少年终于回来,高兴得立即小跑着出来迎接:“您可回来啦,担心死我了!”
哦,这女子叫玉兰。裴谨煞有其事地突然想到了一些东西。
女子高兴完了后注意到了与少年随行的裴谨,小眉一蹙,问少年:“这位是……”
“他是……”少年忽然不好回答,总不能当着面说,这是刚刚的仇人吧。
裴谨见少年支支吾吾答不出来,拱手一笑:“在下今日随家亲来城里游逛。不过在下有错在先,得罪了贵府公子。现在只愿公子原谅,不再记恨在下。”
女子一听吓了一跳。他说记恨,那……让她们公子记恨的事,那是该有多严重……她看看少年,略带生气别扭地转头不看裴谨,裴谨则只好在一旁尴笑。这时,裴谨的马轻声嘶叫,想来是饿了。
玉兰女子笑言:“天色已晚,不如请这位公子一同用过晚膳,小女与当家们说说,让他们遣人送您回去,好不好?”
这提议是不错,不过裴谨清楚自己的身份,一路隐藏起来,想必是要事事小心为慎。
他又拱了拱手,道谢:“小姐的好意在下心领。不过在下不便多加打扰,这就回去了。”他笑得自然,显然是一贯以笑言行的作风。
少年一直聚睛于他。
道了别了,裴谨轻轻一跃,跨上马鞍。他身姿如轻盈的豹,衣上的花纹更显得他高傲不羁。少年和少女怔了怔,才想起要送别这个男人。少女刚要开口,街道不远处就来了一队人。
宅子的当家回来了。
他们来到裴谨马前停下,一名轿夫忽然发话:“什么人,竟然挡路!”
裴谨迎上那嫌弃的目光,眼微眯,勒住的马如它的主人心思一般,一步不动。
“什么事?”
“大人,有一人挡在门前罢了。”
轿里的人探出头,眼睛不大好使,终究还是下人将他扶出了轿。
“爹。”少年朝那人唤了声。
那人好不容易定睛看看马上的人,脸色一开始的疑惑,渐渐的,是苦苦思虑,再最后,他终于恍然大悟,脸色霎时僵硬——
裴谨勾起嘴角,扬笑。
少年与玉兰女子不解地,看他们的当家颤抖着跪下:
“皇上……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
面前的人,无一人不下跪。
字数:3294 鲜花(172)
鲜花(172) 鸡蛋(0)
鸡蛋(0) 鲜花(172)
鲜花(172) 鸡蛋(0)
鸡蛋(0) 鲜花(10145)
鲜花(10145) 鸡蛋(100)
鸡蛋(100)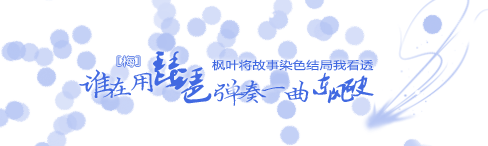
 鲜花(172)
鲜花(172) 鸡蛋(0)
鸡蛋(0) 鲜花(172)
鲜花(172) 鸡蛋(0)
鸡蛋(0) 鲜花(172)
鲜花(172) 鸡蛋(0)
鸡蛋(0) 鲜花(172)
鲜花(172) 鸡蛋(0)
鸡蛋(0)